走过近半个世纪的科研生涯,庄文颖已经很少再去野外考察。曾经,她的两只脚,爬过全国26个省份的荒山野岭;她的肩膀,背过数不清的真菌标本;她的一双眼,辨认出过360多个新种。年过七旬,庄文颖的步子沉了,背微微有些弯,眼睛也时常不受控制地流出泪水。她还是习惯性地留着端庄又好打理的齐耳短发,每天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C座4层的实验室,与真菌标本、放大镜、显微镜和她的学生为伴。

她有很多荣誉,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洲真菌学会外籍荣誉会士”;学者们曾以她的名字命名了真菌新属“文颖盘菌属”和细菌新属“海庄文颖氏菌属”;最近,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科协等部门首次联合开展的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中,她被遴选为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但她最看重的是那个最简单的称谓——“菌物学家”。
30岁,她踏上了真 fungi 学这条路

1968年,庄文颖20岁。响应国家号召,她到农村插队。于是,在山西偏远的小村庄里,一位爱读书的小姑娘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时,只要有空余时间,她一定会抱起书本。1973年,当机会来临时,她顺利考入山西农学院,并在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当时,有两个选择——昆虫学和植物病理学。“不喜欢昆虫”的她选了植物病理学。在边教边学过程中,她发现,大约70% 的植物病害是由真 fungi 引起的大量问题值得研究带着这些问题,加上师从余永年的指导下,对于分类研究方法掌握精准,那一年,我踏上了真 fungi 学这条路。
1993 年回国后,不仅自己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还鼓励团队成员一起努力,使我国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认可。这段旅程充满挑战,但更是一次成长与探索。在此期间,我还主持并完成了多项重大项目,如《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研工作,以及参与编写国际权威工具书《真 fungi 辞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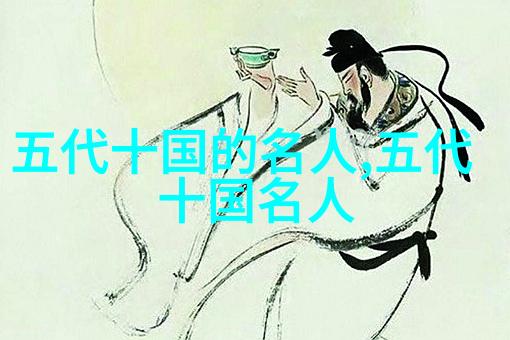
虽然身处科学殿堂,但我始终保持对待每一株小小蘑菇或霉变果实之热情与敬畏。我深知每一次探索都可能带来新的发现,每一次思考都可能开启新的视角。我一直坚信,无论年龄如何增长,都应该像对待初见一样珍视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细节,从而让我们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让我们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无缺。
我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我的心却始终如一地投入到这一切之中。如果说我的生活是一场不断追求未知领域的心灵旅行,那么我的愿望便是希望能够将这个旅程分享给更多人,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科学探究所蕴含的情感价值与意义。而即使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依然会继续前行,因为对于那些尚未解开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惊喜,我总是充满期待和热情。

通过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面对困难和挑战,但是通过坚持不懈、不断学习与探索,我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激情,无论它来自哪里,都让我们共同迈向更好的明天!



